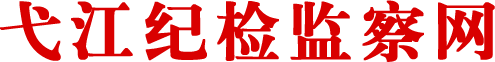梁漱溟(1893—1988年),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,当代文化名人,在国内外享有盛誉,与熊十力、马一浮合称为“现代三圣”。梁漱溟毕生治学,博通古今,学贯中西,著述甚多,成就卓著。他的治学以“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”为目标,不单是求知识,“求知识盖所以浚发我们的智慧识见”,“有智慧识见发出来,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,就是善学”。梁漱溟所谓的“学”,是人生实践之学,指一切做人做事,而不止于学知识。通过研读《梁漱溟全集》,可以真切体会到,梁漱溟的治学与其生命、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。梁漱溟为实现“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”,形成了一系列的治学之道。梳理其独特的治学之道,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“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,方才切实有受用”
梁漱溟认为治学必须用心自学,通过切身自学求得来的学问,才能被消化吸收,融会内化为自家心得,才是真学问。
他在《我的自学小史》的序言中说:“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,方才切实有受用。反之,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,就不会受用。”俗话说“学来的曲儿唱不得”,便是此道理,模仿着唱,不好听,“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,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,才中听”。“学问和艺术是一理,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,知非真知,能非真能”。自学对每个人来说,都至关重要,“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,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”。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,最终都是出于用心自学得来的。因此说,“一分自求,一分真得;十分自求,十分真得。”
他在《朝话》中指出:“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、材料,系统化、深刻化。更扼要地说,就是‘学问贵能得要’,能‘得要’才算学问。”其中得要,就是心得、自得。并进一步说:“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,消化。吸收不多是不行,消化不了更不行。”“在学问里面你要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,这就是有活的生命,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。”读书治学要注重消化吸收,融会贯通,才能成为自家心得。如果只是读死书,或者死读书,即使把很多东西都记下来,只会觉得负担很重,没有内化为自己的东西,无法运用自如。
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,更要“思考到老”
梁漱溟毕生坚持独立思考,他曾说自己是“问题中人”,一直致力思考和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。
梁漱溟曾在198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对于我这样的九五老人,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了。但我丝毫没有颓唐、悲凉的黄昏之感。语云:‘活到老,学到老’,我加一个‘思考到老’。只要我的脑子还能用,我将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继续走下去。愉快而充实地送走这最后一段岁月。”梁漱溟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做的,年过九旬,还撰写出版了《人心与人生》等著作。张岱年曾评价说:“梁漱溟更是一个特立独行,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。梁漱溟考虑问题非常认真。”费孝通亦对梁漱溟的独立思考,对他的治学、为人,“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”。
梁漱溟在《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演》中说:“我不知为何特别好用心思,我不知为什么便爱留心问题,——问题不知如何走上我心来,请它出去,它亦不出去。”他在为纪念北京大学90周年而写的《值得感念的岁月》中说:“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之日起,就爱寻个准道理,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。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,便不肯忽略过去。”梁漱溟喜欢用深思,乐于追究问题,经常沉溺在思想中,亦时时记录其思想所得。他曾将对人生苦乐等问题的思索写成长文《究元决疑论》,刊发在1916年的《东方杂志》,获蔡元培赏识,被特邀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。梁漱溟的一生都在思考,敢于寻根问底,敞开思想,并且他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,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
学会自觉自省,“一个人最怕无自知之明”
梁漱溟主张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要自觉、自知、自省,都应坚持时刻反躬自省,常思己过,方能不断向上自强。
梁漱溟自认为是个很笨很呆的人,资质平常,没有过人之才,但他有一片向上心,自知好学,从不偷懒,平素总对自己有一种要求,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。特别是从十三四岁开始,“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,不论何事,很少需要人督迫”。他认为,“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,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”。梁漱溟还说:“一个人缺乏了‘自觉’的时候,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,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。‘自觉’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!”
梁漱溟在写的《寄宽恕两儿》信中告诫说:“一个人最怕无自知之明,既能自知所短,则其短处之遗害已去一半矣。因随时自觉,此自觉心即此短处之反面也,虽不能就反过来,亦不致顺着短处下去了。”他在《我的努力与反省》中指出,“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,纵有才气,甚至才气纵横,亦白费,有什么毛病无法救,其前途亦难有成就。反之,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会,时时回头照顾,即有毛病,易得纠正,最能自己寻路走,不必替他担忧了,而由其脚步稳妥,大小必有成就,可断言也”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认清自己的不足,才能不断完善自己,有所成就。
亲师取友,“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”
梁漱溟认为亲师取友是最好的调理自己的方法。他从中学开始就结交了一些亦师亦友的朋友,通过与他们在人生观、价值观与学术观上共同探讨、彼此质疑、互相问难,受益良多。
古人云:“智者不能自见其面,勇者不能自举其身。”每个人都难免会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和偏狭,即使看清楚了又不易随时自主地调理自己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梁漱溟提出“亲师取友”的办法。“靠朋友之提醒以免于忽忘,这是一层;更进一层,就是靠朋友的好处,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。”
梁漱溟1917年受到蔡元培的邀请,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六七年间,结识了梁启超、林宰平、伍观淇、熊十力、李济深、陈铭枢、李大钊等,他们大部分比梁漱溟大10岁或20岁,他们之间的关系多在师友之间。还有许多与梁漱溟年龄相仿的朋友,多是北大的学生,如冯友兰、朱谦之、陈政、罗常培、冯庸等,其中与陈亚三、黄艮庸、王平叔、张俶知等,“关系甚深,踪迹至密,几于毕生相依者”。据梁培宽撰的《先父梁漱溟与北京大学》记载:梁漱溟与叶麟、朱谦之、黄艮庸他们,虽为师生关系,但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,只是朋友,“四人性格见解并不相同,议论每多不合,但总觉得彼此相对是第一乐事”。梁漱溟认为他在北大期间,从蔡元培和诸同事、同学所获益处,直接间接,有形无形,说之不尽,于是得以经过自学钻研,在学识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,并走向成熟。
“我的生命就在于责任一念”,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躬行实践
梁漱溟做学问不是为学问而学问,实由自己的生活或生命遇到的问题,完全没有把学问当做一个客观的外在的对象来治力和追求,学问是解决人生困惑的副产品,是为解决毕生思考的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服务的。他始终躬行实践。
梁漱溟在1951年写给其外甥邹晓青的信《寄晓青甥》中说:“我的生命就在于责任一念。处处皆有责任,而我总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。所谓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问题。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的问题看。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,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。在最大的问题中,我又选择其最要紧的事来做。”
梁漱溟一生都在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。如他始终关心农村,关心中国,他主张从建设乡村入手,寻求一套建国之路。他的《乡村建设理论》就是要为中国社会寻找一条出路而写的理论著作。梁漱溟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人,为实践自己对教育工作的认识,为探索中国自救之路,1924年辞职离开北大,在广东筹办“乡治讲习所”,在河南促进村治,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运动,这些都代表着梁漱溟一种实践精神的努力成果。